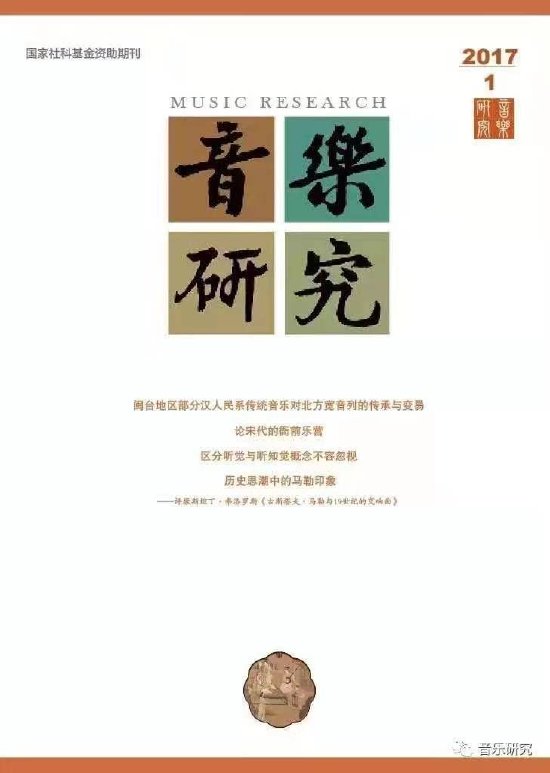亚历山大·斯特洛克在上海的音乐活动研究——以《字林西报》为主要资料来源

教育
关注目前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著述中,都部分地提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音乐家在上海的演出活动,这些演出活动对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以及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而西方音乐家来沪的演出活动,其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即为音乐经纪人的活动。笔者因博士论文的写作,查阅近代上海西方人创办的《字林西报》,发现其刊登了大量亚历山大·斯特洛克(Alexander Strok,以下简称:斯特洛克)邀请而来的世界著名音乐家的演出活动。这些音乐家在上海的演出活动作为珍贵史料,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斯特洛克的引荐成为世界著名音乐家来沪巡演的重要媒介。由此,斯特洛克对西方音乐在近代上海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素有“英国官报”(Offician British Organ)之称的《字林西报》,是近代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其刊载内容包括国际新闻、中国新闻、内地通信、上海地区新闻、外侨生活等,其中还刊载了大量外侨音乐文化生活的内容,尤其对音乐演出活动的报道,更是不吝笔墨。以1927年为例,该报一年内就刊登了225场音乐会的节目单,平均1-2天就有一场音乐会上演,当时上海租界音乐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因而,《字林西报》对近代上海租界音乐演出活动的刊载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与涵盖性,而对斯特洛克在上海音乐活动的详细记载与报道目前也主要见于《字林西报》。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字林西报》刊载的音乐史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以斯特洛克为研究对象,对其在20世纪上半叶于上海所进行的音乐活动进行初步的整理与分析,以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史料补充。
一、斯特洛克:从演奏家到经纪人

(前排左起第一位为斯特洛克先生 图片出自《字林西报》1926年3月22日第18版)
斯特洛克(Alexander Strok,别名Avray,1877-1956),出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1913年11月加入上海公共乐队,任乐队第二小提琴手,直到1916年一直是乐队成员。据笔者查阅《字林西报》所刊载相关资料获知,1913年11月,斯特洛克开始作为一位小提琴教师招收私人家教,教授小提琴。从当时发布的广告信息来看,斯特洛克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艺术学校,以下是当时的海报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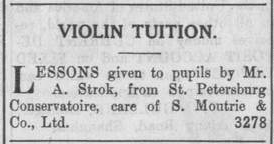
(《字林西报》1913年11月8日第1版)
斯特洛克作为音乐经纪人的生涯,据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一书中介绍:斯特洛克了解到,通过公共乐队的演出活动,上海培养出一批音乐爱好者,而且他们因为远离故乡,对欧洲的艺术如饥似渴,因此他结束了自己艺术家的生涯,转而投身娱乐事业。在上海最繁荣的20世纪20、30年代,斯特洛克招聘了数位欧洲著名音乐家来上海演出,成为远东著名的音乐经纪人。从当时《字林西报》刊载的有关资料来看,1918年开始,斯特洛克才开始作为音乐演出经纪人的身份,邀请世界著名艺术家来上海献艺,这样的生涯一直持续到1940年左右。当然,这期间斯特洛克作为音乐经纪人的活动不仅局限于上海,还包括北京、天津、广州等地以及其他远东地区(如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1956年,斯特洛克在日本东京故世,享年70岁左右。
除介绍音乐家来沪演出外,斯特洛克也作为音乐家教活动的经纪人,为著名音乐家作宣传,介绍音乐学生。据《字林西报》所刊载有关资料显示,斯特洛克曾作为经纪人为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Boris Zakharoff)先生招收家教学生,广告信息显示:斯特洛克荣幸的宣布,彼得格勒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鲍里斯·查哈罗夫先生将会在1月份起招收钢琴初学者以及有一定钢琴基础的学生。以下是当时的海报信息:

(《字林西报》1929年1月3日第19版)
因此,斯特洛克作为音乐经纪人的身份是两重的,他不但介绍世界著名音乐家来沪巡演,而且还致力于为著名音乐家做宣传,介绍家教学生。然而对于斯特洛克其人,我们还有很多疑问,他为什么放弃职业小提琴家的身份,而转做音乐经纪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他的选择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自身的所谓经纪活动能力和素质是否适合或达到经纪活动的相关要求?等等。笔者认为,斯特洛克作为工部局乐队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他的思想与行为受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当时上海的“局势”对于其能动性对象的选择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从内在的方面来看,斯特洛克本人作为经纪人的活动能力及其敏锐精明的个性特征也是其成就经纪人身份的重要因素之一。
1、作为外因的租界“西方社会”局势
1843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一批批英、法、美等外国人从异国来到上海,上海成为西方人租地建筑居所的中国近代城市之一,一时间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纷纷建立。上海租界成为中国租界史上开辟最早、历时最长、面积最大的租界。比天津英租界早15年,比汉口、广州等租界早16年;它比天津英租界与汉口英租界分别长16年和33年;上海租界的界域面积也最大,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总面积是其它23个租界总面积的1.5倍。另外,上海租界的外国侨民也是最多的。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改为公共租界后,其外国侨民的数量迅速增加。1905年,外国侨民人数超过一万以上,1925年的人数超过三万,1931年超过六万,1937年以后,由于日本人的涌来,上海外侨的人数迅速激增,至1942年,外国侨民的人数达到150931人,获致顶峰。这些外国侨民包括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日本人以及大量的犹太人和无国籍俄国人等。由此,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租界城市,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西方文化输入的重要舞台。
居住在上海租界的西方人,他们对故国的思念让他们时刻想象塑造一个“故国的家园”。汤亚汀在对殖民宗主国英国的论述中认为,英格兰家园是这些移民的理想之地……人们要以伦敦式的音乐会生活——即便是一支业余管弦乐队也可以凑合——在上海租界再造一个他们记忆中的如同英国家园这样的理想之地,一群流散殖民者的“想象的家园”。因此,西方音乐文化在“海外西方聚居地”的上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音乐文化语境,跑马厅、剧场、音乐厅、俱乐部等都是这一文化语境的产物。而这样的一种“局势”,为世界著名音乐家的远道来访提供了可资展演的空间和潜在的受众,所有这些都为音乐经纪人的活动提供了现实的物质空间和动机导向。
2、作为内因的经纪人的敏锐个性
对于斯特洛克作为经纪人的个性,由于史料的局限,虽不能窥见其全面,但在阿图尔·鲁宾斯坦自传《我的漫长岁月》的“东方大巡演”章节中有了一定的交代。书中提到,由于鲁宾斯坦从哈尔滨拍的电报只提及到达下关的日期,没提及具体的钟点。斯特洛克认为鲁宾斯坦会乘坐大板开出的豪华车下午3点到达,因此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而鲁宾斯坦却在3点之前早已抵达。以下是后来鲁宾斯坦与斯特洛克的对话:
鲁宾斯坦说:“依我看,你只要通过扩音器解释一下,说我已经抵达,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正在饭店休息。”斯特洛克阴沉着脸,说道:“我只会六七个日语单词,而且这样一来,简直会要了咱们生意的命。”
突然,斯特洛克的脸上阴云消散、阳光明媚起来。说道:“我们还有几小时。如果你们穿上衣服,拿上两三件行李,我们坐火车一小时以后就可以到横滨。然后我有办法让咱们坐上去东京的豪华特快,我就假装是跑到横滨去迎接你们的。”
在乘坐豪华快车的过程中,因为斯特洛克没有支付从大阪起的全程卧铺费,因此途中遇到些麻烦,而斯特洛克的几句日语,已经足够让列车员眉开眼笑。
到达东京后,斯特洛克在介绍鲁宾斯坦的言语中,炫耀地、夸张地、咂着嘴唇嚷嚷道:“有谁见过直接从巴黎来的人抵达时穿得像他们俩那样?”这让上千人大摇其头。
从以上言语对话及神情的描述中,足以见得斯特洛克是一位机智、聪慧,且善于经营和谋划的经纪人,这样的个性特征,又加之了解到上海的西方人对西方音乐的渴求,使他决然从器乐演奏家的身份转作音乐经纪人。
二、斯特洛克操办的演出活动之分析
斯特洛克虽然也是一位家教活动的经纪人,但他的活动主要还是体现在他作为演出活动经纪人的身份,即作为演出商和经纪人的双重身份为近代上海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笔者据《字林西报》所刊载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18至1940年间,斯特洛克作为演出经纪人先后邀请62位音乐家、1个歌剧团、 1个舞蹈团来沪演出,23年间共演出节目269场。以下笔者将对斯特洛克操办的知名音乐家的演出活动从演出主体、演出地点、演出的商业性等方面作一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1、俄国音乐家成为重要演出主体
据笔者查阅《字林西报》的资料来看,1918年开始,斯特洛克就已着手操办各种音乐演出活动,1918至1940年间,斯特洛克所邀请的62位音乐家中,其国别分布如下:俄国音乐家31位(津巴利斯特、戈多夫斯基、林文茨基、莫伊谢耶维奇、汉森、西比里亚科夫、鲁宾斯坦、切尔卡斯基、埃尔曼、克鲁采等),英国音乐家7位(弗洛拉·曼、希拉里·纳皮尔等),西班牙音乐家6位(阿根缇娜、塞戈维亚等),意大利音乐家4位(帕器、弗莱塔等),奥地利音乐家3位(克莱斯勒、费尔曼等),美国音乐家3位(加里森、蒙茨等),匈牙利音乐家2位(西盖蒂、库贝利克),德国音乐家1位(玛格丽特·内特克罗伊),法国音乐家1位(蒂博),立陶宛音乐家1位(海菲茨),荷兰音乐家1位(扎尔斯曼),爱尔兰音乐家1位(麦考马克),波兰音乐家1位(费尔德曼)。从以上统计来看,俄国音乐家占有50%的比重,而邀请来的两个音乐团体分别为俄国大歌剧团与美国丹妮肖恩(Denis Ted Shawn)舞蹈团。因此,斯特洛克邀请而来的音乐家以俄国音乐家为重要演出主体,而且,来沪演出的部分俄国音乐家的演出活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如俄国钢琴家本诺·莫伊谢耶维奇(Benno Moseiwitsch)与小提琴家埃夫雷姆·津巴利斯特(Efrem Zimbalist)等。
莫伊谢耶维奇,俄国著名钢琴家(1937年入英国国籍),曾在维也纳师从波兰钢琴教育家、演奏家莱谢蒂茨基(Lescheitizky),后者为著名奥地利作曲家、钢琴家车尔尼(Czerny,Karl)之高足。1909年在伦敦首演,引起轰动。1914年在欧洲大陆巡演。1928年前后、1930年初等多次来远东巡演。23年间,莫伊谢耶维奇先后5次分别在市政厅、法国总会、夏令配克戏院等场所演出,共演出节目16场,是来沪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位音乐家。之所以他的演出最多,其原因之一,是他的岳父与岳母于上海定居,他需要来探望与慰问。据《字林西报》载:“1933年左右的演出季中,莫伊谢耶维奇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举行57场演出,在爪哇举行32场,在印度举行12场,在日本举行14场,在新加坡举行4场。而且在澳大利亚等地的演出,每场音乐会都有上千人的上座率。”《申报》对莫伊谢耶维奇音乐会的宣传与报道指出:“莫伊谢耶维奇在欧洲、美洲的各大都会中举行过很多音乐会,均受到热烈欢迎,且都取得很完美的成功。他的艺术醇化能力不可思议,难用笔墨来描写。”这是一位中国人对演出活动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莫伊谢耶维奇有着高超的演奏技巧和对艺术的诠释能力。津巴利斯特于1901年就读于圣彼得堡皇家音乐学院,为奥尔教授之高徒。1907年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并获得金质奖章与鲁宾斯坦奖。后作为小提琴演奏家于世界各地巡演。1922年4月,津巴利斯特首次访问上海。1924年以及1932年再次来沪巡演。23年间,津巴利斯特在上海共举行13场音乐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8月14日起,津巴利斯特与工部局乐队合作在兆丰公园举行4场音乐会,观众们踊跃参加。第一场音乐会的人数就超过了1500人,演出取得重大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世界著名音乐大师公园音乐会的先例。
之所以以俄国音乐家为重要演出主体,一方面,从斯特洛克的艺术经历来看,因其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艺术学校,对俄国的艺术环境与俄国音乐家更为熟知与了解,这对介绍俄国音乐家来沪巡演提供了有力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音乐家来沪定居,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音乐文化生产与发展的主力军,上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俄国音乐家从事演艺、教学和生活所建构的“音乐飞地”。这样一种上海音乐文化生态对巡演的俄国音乐家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因此,在斯特洛克的积极引荐下,大批世界知名的俄国音乐家得以来沪巡演。
2、兰心大戏院与市政厅为主要演出场所
笔者根据《字林西报》所刊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3年间所演出的269场音乐会中,兰心大戏院85场、市政厅71场、夏令配克戏院68场、卡尔登戏院12场、大光明戏院5场、兆丰公园5场、新光大戏院4场、奥德翁戏院4场、南京大戏院1场、法国总会1场、虹口公园1场。因此,兰心大戏院与市政厅以及夏令配克戏院成为重要的演出场所,尤其是兰心大戏院与市政厅为西方音乐的演出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汤亚汀认为:作为上海现代西方音乐会标准音乐厅的只有兰心大戏院与工部局市政厅两处。如果将23年的演出活动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1920年以前);第二时段(1921-1929);第三时段(1930-1940),那么,各个时段的主要演出场所略有变动:第一时段为兰心大戏院;第二时段为市政厅;第三时段为兰心大戏院。为什么三个时段的主要演出场所会有变动?为什么在第三时段又转入兰心大戏院?基于这样的疑问,笔者对当时的剧场情况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时段的兰心大戏院为第二代兰心大戏院,剧场结构模仿欧洲剧场,且十分豪华,音响质量也颇高。藤田拓之认为:进入20世纪后,兰心大戏院在上海外国人的社会中具有了相当大的文化权威,成为身着晚礼服的上层社会人士的社交场所……而且演出层次的高档难得一见。因此,斯特洛克选择兰心大戏院为主要演出场所,显示出其操办演出活动的层次和规格的高度权威性。第二时段因上海城市文化中心的西移,兰心大戏院日显破旧,因此这一时段的主要演出场所转入市政厅。另一方面,此时段的市政厅正是工部局乐队交响音乐会的主要演出场所,已形成一定数量的固有受众群体,斯特洛克选择其作为主要演出场所在受众层面上已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三时段,老市政厅大楼因设施陈旧遂被拆除,兰心大戏院成为主要演出剧场。这时期的兰心大戏院为第三代兰心大戏院,其建筑结构为钢筋水泥结构,剧场规模较之前扩大,且在其设计、照明以及音响方面等更具有专业性。另外,30年代的兰心大戏院租金较当时的大光明剧院、卡尔登剧院便宜很多,且音响效果更好,以它作为主要演出场所,不失为明智之举。
由此可见,斯特洛克对邀请而来的音乐家的演出场所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选择代表上海现代西方音乐会标准音乐厅的兰心大戏院与工部局市政厅为主要演出场所,显示出其所操办的演出活动既有西方专业音乐会的高规格特征,又考虑其所具有的实用性和经济性特征,因此,斯特洛克对演出剧场的选择是现代性、商业性、实用性兼备的经济之道。
3、演出活动的商业性特征
斯特洛克操办的音乐演出活动作为一种音乐现象,同时也体现出一种商业化特征。其一,音乐经纪人的活动是一种商业行为,他们通过这种中介性的商业活动,获得经济收入。正如有关学者对音乐经纪人的定义中认为的那样:音乐经纪人是指在音乐市场中从事相关艺术家包装、艺术家营销、音乐会宣传等商业中介活动而收取佣金的自然人、法人。因此,音乐经纪人一定意义上为音乐活动的中介人,也是安排与组织各种音乐活动的法人代表,其主要是通过商业手段将音乐文化产品进行宣传与交易,并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也由此,此种音乐活动的商业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二,从当时《字林西报》刊载的演出海报来看,这些音乐家的演出活动门票价格要比普通寓居于上海的音乐家或非经纪人操办的演出门票高出2倍或3倍有余。如1925年4月,斯特洛克引荐的花腔女高音加里森(Mable Garrison)在市政厅演出,门票为6美元、4美元、2美元。而同年4月,彼得格勒剧院的戏剧女高音阿尔佩特·罗萨诺夫(Alpert-Rosanoff)在市政厅的入场费仅为2美元、1美元、50美分。又如1931年5月,约瑟夫·西盖蒂(Joseph szegeti)在夏令配克戏院演出,门票为5美元、2.5美元 ,而同年5月31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音乐会票价仅为1.5美元、1美元和60美分。再如,1932年1月,斯特洛克引荐的舞蹈家特雷西纳(Teresina)在夏令配克戏院演出,门票为6美元、4美元、2美元,而同年5月,钢琴家拉利亚·福克斯(Lalia Fuchs)女士在美国妇女俱乐部独奏会的入场费仅2美元。 因此,斯特洛克所邀请而来的音乐家的演出活动明显体现出其“商品”的性质。
斯特洛克通过这种商业化的运作模式,邀请大批世界知名音乐家来沪巡演,虽然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佣金,但在客观上却成为繁荣近代上海音乐文化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音乐家的访沪演出活动成为当时租界音乐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斯特洛克对近代上海音乐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
三、斯特洛克音乐活动的历史贡献及思考
斯特洛克作为近代上海租界著名音乐经纪人(实际上,他的活动不仅局限在上海租界,北京、天津、广州等地以及远东其他国家都有他的足迹,如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前已有所述),他的音乐活动在繁荣近代上海音乐文化市场,促进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同时,也引起我们一定的思考。
1、繁荣近代上海音乐文化市场
西方社会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其消费文化观念就形成一种轻日常消费,重公共消费;轻物质消费,重休闲娱乐和精神性消费的特征。后来,伴随两次科技革命,西方“消费革命”崛起,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布满了眼花缭乱的电影院、剧场、音乐厅等休闲娱乐设施。近代上海租界,从其性质来讲,即是一个“西方小社会”,这里同样建立起像西方一样的剧场、音乐厅、俱乐部等娱乐休闲场所,如兰心大戏院、维多利亚剧院、夏令配克戏院、奥德翁戏院、阿波罗剧院、法国总会、百乐门等,这些休闲场所的建立是西方消费观念引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为世界著名音乐家的远道来访提供了空间和观念的支撑。斯特洛克作为音乐经纪人,将大批世界著名音乐家和演出团体引荐到上海巡演。从《字林西报》刊登的演出海报来看,当时上海著名剧院如:兰心大戏院、市政厅、夏令配克戏院、南京大戏院、卡尔登戏院、奥德翁剧院等都是这些世界级大师的频繁活动场地。斯特洛克深刻了解到上海租界的音乐文化消费观念,并通过这种商业化的行为,将音乐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观众的同时,实现了经纪人、音乐家和受众以商业性为特征的关系链,从而繁荣和拓展了近代上海的音乐文化市场。
2、促进西方音乐在近代上海的传播
斯特洛克作为音乐经纪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音乐在近代上海的传播。其一,斯特洛克所邀请而来的音乐家的演出活动将大量的西方器乐与声乐作品介绍到上海,器乐包括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时期及印象主义时期等音乐家的钢琴、小提琴作品;声乐包括威尔第、比才、德里布、普契尼、古诺、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罗西尼、列昂卡瓦罗、马斯卡尼、哈列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作曲家的歌剧或声乐作品。这些世界知名提琴家、钢琴家、声乐家中尤以钢琴家马里奥·帕器(Mario Paci)的贡献最为突出。马里奥·帕器来沪后在夏令配克戏院与兰心大戏院共举行了三场钢琴音乐会。三场音乐会后,马里奥·帕器因其出色的能力被聘为上海公共乐队(后称为:上海工部局乐队)指挥。在他的领导下,工部局乐队达到了它最为繁荣的鼎盛阶段,有了“远东第一乐队”的称号。在他担任指挥的23年间,工部局乐队承担了引领上海租界公共音乐生活的重要角色。据笔者对《字林西报》所刊载的相关资料的统计来看,23年间,工部局乐队每年的演出场次都要超过《字林西报》所刊登的所有音乐演出活动的60%以上。可见上海工部局乐队在当时上海租界音乐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没有斯特洛克的引荐,就没有马里奥·帕器先生的到来,没有马里奥·帕器,工部局乐队的发展以及租界的音乐生活可能会是另一种发展态势,马里奥·帕器是斯特洛克作为音乐经纪人之后续辐射作用的重要体现者。其二,中国观众开始作为重要的受众群体,参与到世界著名音乐家的演出行列。1931年5月19日晚,小提琴家约瑟夫·西盖蒂在夏令配克戏院举行第二场音乐会,当时《字林西报》评论道:“尽管外面下着大雨,夏令配克戏院仍座无虚席。西盖蒂先生的访问,为当地的音乐爱好者带来了很多欢乐,其中,中国学生是这些音乐爱好者中比重较大的一部分”。可见,部分中国人已经成为西方音乐的爱好者,他们的参与,也进一步促进了西方音乐在近代上海的传播。
一位访问上海的匈牙利小提琴家费里·洛伦特(Fery Lorant)先生,在接受《字林西报》记者的采访中表达了他的惊讶之情。他说,在一个与他的思想完全不同的国度里,将会有如此多的音乐圈子。在这里会有对美好音乐真正感兴趣的人们。他评论了去听工部局乐队排练时的情况:“我发现了一个纪律严明的交响乐团,它们当中的一些成员水平很高,以他们的水平,可以让自己留在任何欧洲音乐的中心。我也非常惊讶地看到大师对音乐的爱和真正的艺术兴趣,马里奥·帕器经营着乐队并且安排各种演出活动,演出的节目包括很多音乐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不容易演奏,而且也为演奏者和观众都创造了一种好的音乐文化氛围。而越来越多的著名艺术家的远道来访,我认为,斯特洛克先生的积极倡议,必须被看做是上海音乐文化崛起的标志 。”由此可见,斯特洛克作为音乐演出经纪人,对近代上海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一个不得不提的事实是,斯特洛克作为近代上海租界著名音乐经纪人所操办的音乐演出活动,其本身是有着某种“殖民性”的。世界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东方大巡演”的自述中描述到:自来到上海几天后,仍没看见谁像中国人,斯特洛克一家人带着轻蔑的表情回答了中国人在哪里的问题,说城南没有铺路面的街道上和那些拥挤不堪、只能描述为贫民区的地方,可以见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这样的回答具有多么强烈的讽刺性!在当下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这种现象也带给了我们一定的思考。近代上海所形成的租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否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输出理论的产物?此种性质的文化输出是否以文化生产与流通过程的不平等为其重要特征?或是一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从而形成西方消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形成以西方音乐传入为主的单向性音乐文化交流的生态?所有这些应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另外,对于斯特洛克先生音乐活动的相关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如他在北京、天津以及广州所操办的各种音乐演出活动等,以及其所涉猎的日本、新加坡等地的音乐活动等资料的挖掘也是近现代研究东方音乐或世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同样应当加以关注。
通讯作者--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刘红梅